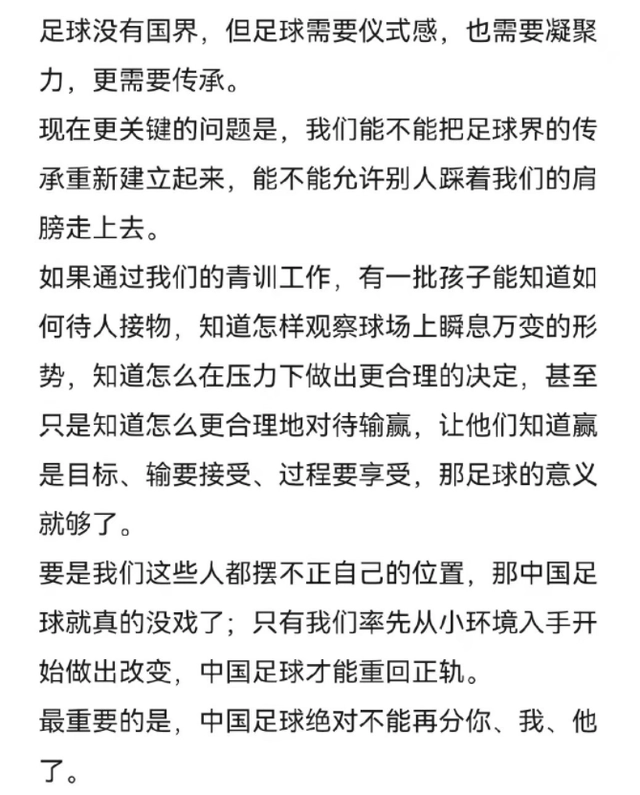何秉迪先生
何先生晚年的回忆录《读史读世界六十年》,有很多关于他学术生涯中的师友关系的叙述,尤其是老清华大学(1930年代)的关系。 何先生对清华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求学期间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清华文化和清华精神。 晚年,他多次回到清华校园参观,最后一次是2010年在西台阶讲学。 仔细阅读他所写的清华大学昔日的风采和魅力,是今天所无法比拟的。 令人敬佩,更令人震惊。 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文章中难免显得要靠师友来宣传自己,但这也是他自己的风格。 本文节选自《读历史读世界六十年》第七章“清华大学(下)”。 原标题为“‘天’与‘灵’”,稍作删减。
如果我此生能进入“天堂”,那么“天堂”只能是1934年至1937年的清华大学花园。天堂不仅要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还要提供一个精神环境,让寄居者可以不断提高自律,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几次政治风暴都无法抹去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人间“伊甸园”清华度过的。
1934年秋九月,当我作为一年级学生走进清华大学校园大门时(校墙已被拆除,南门已无法进入),空旷的草坪北侧矗立着古罗马建筑。万神殿风格的礼堂。 无论是它的四根古希腊爱奥尼亚(Inic)石柱,古罗马青铜穹顶,还是整个建筑及其各个部分的几何形状、线条、重叠和突出的层次、三角形、拱形等。 典雅的设计,以及雪白大理石与浅红砖的结合,都给人一种庄重、庄重、古朴、对称、色调和谐的多维美感。
20世纪70年代,我受邀到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演讲。 我住在托马斯·杰斐逊总统(1743-1826)设计的罗马万神殿风格礼堂的左侧。 宿舍里,所以有充足的机会欣赏这位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杰作。 我觉得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的造型、线条、曲面似乎有点太“复杂”了; 而且这个礼堂的东、西、南都是宿舍的走廊,所以礼堂本身就有些“受限”的感觉。 相比之下,清华大学礼堂在南方无限的阳光和开阔草坪的“支撑”下,显得格外“美丽优雅”。 也许是工作上的情绪,但我一直相信清华大礼堂是中国最美的古典西式建筑。
礼堂东北侧的小溪对面就是图书馆,外观非常优雅、柔和。 图书馆后面的北校区是最西式的教授住宅。 向西、向北,绕过古色古香的“水木清华”工字厅和古月堂走廊,就到了田径场和“罗斯福”体育馆(因罗斯福总统决定使用美国超级体育馆而得名)。任内的教制。庚子赔款归还中国)。 再往西看,可以看到颐和园的塔尖和玉泉山(20世纪30年代,只有清华学生才能从喷泉饮水池喝水,堪称“天下第一泉”)。 清华园虽然没有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但春假期间,三院门前由万朵盛开的榆叶梅组成的粉红色锦帘,增添了几分“少年维特的烦恼”; 夏禾工字厅旁的常春藤,生物馆前的嘉溪垂柳,都曾引起许多青年诗人的思索。
民国时期的西方演习
当时所谓的四大建筑——礼堂草坪西侧的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被外界批评过于奢侈、浪费。 殊不知学校当局是有远见的,希望一劳永逸。 该建筑不仅外观设计精美,内部设备也是最先进的,在当时(乃至解放后)全国仅见一处。 例如图书馆中西阅览室的软木地板、图书馆的钢架和厚玻璃地板、暖气和卫生设备等,都给人长久的享受和永恒的美感。 正是因为清华大学优美、舒适的物质环境。 只有远道而来的莘莘学子,都会情不自禁地在心底暗暗发誓:绝不会辜负留在这人间天堂的机会和特权!
清华关心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 校园内有四个学生食堂:第二、第三、第四校园食堂和女生食堂。 此外,还有所谓的清寒食堂,整餐费用不超过10毛钱或12毛钱。 1934年秋天我入学时,我住在第二校区。 第二校区是唯一一个没有水泵的老宿舍,但它的食堂却很有特色。 最受欢迎的是软炸、微焦的肉片,不知为何被称为“叉烧”。 米饭和馒头都足够了,全肉、半肉和素菜的价格也很合理。 不到20美分就可以吃得饱饱的。 如果和三四个朋友一起吃就更好了。
第二年我们搬到了新建的七院,经常在四院新建的大食堂吃饭。 座位多,快餐服务,极其方便。 我和生物系的林从民、舍友的黄明新以及其他南开老朋友一起吃饭时,经常点西红柿炒鸡蛋、炒猪肝肾、软炸里脊、炒大白菜等菜品。配肉片、木薯肉。 每人大约两毛钱。 为了听从父亲的吩咐,我除了吃饭和买书之外,什么都得省着。 所以寒假考试的时候,我有时也是一个人吃饭。 我先吃了几口红烧肘子(不大,24毛钱),然后点了半素菜。 有时放学换换胃口,去倪家店点一碗葱花肉片生白菜汤面和一个肉饼。 没想到,1938年我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获得哈佛燕京社500元研究生奖学金后,发现我搬来的倪氏店里有很多燕京顾客点“何先生面”。清华! 可见,任何简单的事情只要你花点心思,就永远不会出错。 能不能好好说话,最好就看锅是否“热”了。
清华大学共有三个教职员工厨房。 西吉厨房的饭菜比大食堂的稍好一些,一般是针对单身助教和老师的。 我偶尔也会去那里吃几顿饭。 东记很讲究。 食物有大餐厅的味道。 那里只有外卖,没有桌椅。 只要有耐心,等到柜台式的小“桌面”空出来的时候,嘴馋的人还是能吃到一顿满足的饭菜。 我不知道为什么历史系比我高两级、来自浙江晓峰的申建几乎总是占据那个一尺半见方的柜台。 他一年四季都穿西装,但一穿西装,就“变身”成中式西装了。 。 他利用清华大学陆军部档案写了一篇论文(1936年),很快发表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上。 另外,公子亭西餐厅最重要的常客就是吴宓教授。 我三年级的时候,有两次从他那里收到过食物。 第二道主菜是一大盘12片薄烤牛肉。 主人吃了不到两片,剩下的我都吃了。 随后,我在田径场上慢悠悠地走了至少半个小时,才回到房间。
清华合作社有生活用品、水果、茶叶、咖啡、汽水、糕点等物品。 法式面包店的糕点价格比较贵,但是非常好吃。 英国商人的柠檬山海关牌汽水是标准的老品牌,法国商人马吉的彩色樱桃和柑橘口味的糖醋汽水售价1.4美分一瓶,相当于一顿饭的价格。 北京附近的水果有鸭梨、小白梨、亚光梨、紫葡萄,还有各种吃不完、一般人都不愿意吃的柿子。 在北方长大的人喜欢吃北京的紫萝卜,而我和黄明欣更喜欢吃天津小刘庄的青萝卜。 一天晚上,我们在屋里嚼着青萝卜,喝着浓茶。 当老寇打开门过来给我们倒开水时,他喊道:“你们两个,这是怎么回事?!” 每年寒假结束后,林从民都会从烟台带来一大篮梨、苹果,与南开、六合等各级朋友分享。 这种喜悦是一生难忘的。
清华大学有着重视体育的传统。 男生的淋浴全部设在体育馆而不是宿舍,只是为了“强迫”学生运动出汗后才能洗澡。 每学期三块钱的洗衣费还是很合理的。 马约翰先生年老力壮。 1939年寒冷的冬天,他要求我们像他一样只穿背心和内裤,在田径场上跑800或1500米,然后再进入体育馆做其他体操。 除了打篮球、足球、排球之外,我们还练了木马、单杠、双杠,但都练得不够。
记得在南开初中的时候,我最喜欢各种运动。 1932年秋天,我获得了B组百米第一名,并在初冬参加了往返八里台的越野比赛。 我挂上了鞋钉,停止了运动,专心准备报考清华大学。 在青岛山东大学的一年(1933-1934)期间,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有能力连续打篮球四十、五十分钟。 南开是极少数拥有棒球场的中学之一。 我在南开中学的棒垒球训练使我在清华大学的第一年就成为了棒球队的一员。 校队成员免修体育课,但清华棒球队以来自夏威夷的华裔特殊学生为主。 没有人教我防守、击球、盗垒等高级技能。 第二学期我退出了校队,因为很无聊。 。 那时,最常见的出汗方式就是参加“斗牛”——无论人数多少、规则如何,随意抢、打、投篮球。
1914年的清华足球队
总的来说,我在清华的三年里,并没有进行过什么特殊的训练。 然而,我的体力在青少年时期逐年增强。 除了游泳之外,我各项运动的水平绝对高于平均水平,略低于校队。 例如,1937年春天,我穿着网球鞋跑100米,跑出的时间是12.2秒。 夏翔先生颇为惊讶。 他说这是他在校队之外所知道的最好成绩,并问我为什么不多练习。 如果我能突破12秒,我就能参加学校的400米接力队。 今年春天,肺活量、双杠、双手木柄向上站立三个动作计算的总分是745分。夏先生说,他已经达到了国家标枪运动员彭永新的水平。

然而,“7月7日事件”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定期锻炼身体的机会。 即使在海外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也始终无法重新燃起锻炼的意愿。 我的体力始终无法超过20岁时的巅峰,着实让我感叹。 。 然而,自称“普六仙法”的中年老人杨连胜始终无法忘记自己曾经是一名“斗牛士”。 1938年秋,我与日本司徒雷登秘书、北京燕京大学校长、燕京历史学会会员肖正义先生第一次见面后,对陈云表示惊讶。清华大学七级大四学生陈岱荪先生的表弟:“我以为何丙弟是个江南文弱书生,没想到他是个身高六尺的关西人。”
虽然清华的自然环境、物质设施、生活、阅读、体育等条件都十分优良,但最令人难忘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精神。 正如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当我们踏入清华大学大门,看着礼堂和周围优雅、简洁、和谐、“古典”的美,我们不禁感受到精神上的自强和决心。践行自强不息的古老格言。 (也是学校的座右铭)。 60多年后回望,图书馆柔美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服务精神和效率:出版不到一年的西方新书往往被清华大学编目,或立即作为指定参考书目,或已被清华大学收录。插在图书馆的钢架上。 例如著名外交史学家兰格在美国出版的两卷本《帝国主义外交,1890-1902》直到1935年中期才在美国出版。 我从三年级(1936年初秋)就可以读了。 这必须归功于刘崇宏大师对书目、书评的勤勉审阅、精心挑选,以及编目组主任毕树堂先生工作的极度认真。 一科一课就这样了,剩下的就可想而知了。
20世纪30年代清华精神的最高典范是校长梅贻琦先生(韩岳)。 行业老师刘冲红对梅校长性格最中肯的分析:
他行事谨慎、正直、坚定不移。 他善于辨别事情的轻重,对大局有清醒的认识。 ……实事求是,真诚待人。 最令人敬佩的就是他的人格。 他个人志向高尚,严肃沉着,富有幽默感。 几十年来我一直节俭朴素。 对于清华的巨额资金,他是一丝不苟。 (摘自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新109期(1989年10月31日)第28页)
1934年初秋我们入学后,最初只看到了他优雅、善良、谦逊的一面,近乎木讷,还有“过度”的谨慎。 正如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描述了校长演讲的特点:
大概或者或许,
但我们不敢说,
但学校始终认为,
恐怕这似乎不可能。
……
与当时北大蒋梦麟所倡导的“校长办学”口号(逻辑上暗含校长与教授的对立)有很大不同。 清华传统的“教授治校”原则(这部分源于早期教授与政治校长的斗争),实际上已成为校长与教授相互尊重、紧密合作、相互尊重的最和谐、幸福、高效的新局面。共同管理学校。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不仅是学校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篇章。
1941年清华大学建校30周年,校长与各学院教务长、院长合影留念。 右起:叶其荪、冯友兰、吴又训、梅贻琪、陈岱荪、潘光旦、石家阳。
回顾战前在清华的三年,我只总体感觉受到了清华精神的启发,但具体是在哪些方面、如何受到启发,却并不清楚。 最近,我仔细阅读了梅校长的遗作《大学解读》(《清华大学学报》1940年4月第13卷第1期)并补充反思,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简单来说,梅大师的文章贯通古今中西,具有最高的意义。 他认为,普通大学仅仅提供书本教育是不够的。 “普通教学方法无法顾及”的是学生的意志和情感,而这两方面都取决于“教师的表率”和“学生的自身修养”。 只是“作为一名教师,在这两方面都能有相当的修养,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然的表达,无形中向学生学习。” 文章进一步指出“个人修行的成功,一部分是靠自己的努力,一部分是靠朋友的鼓励”。 美师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虽然简单易懂,但其中蕴含的智慧和真理只能来自对普通高等教育优缺点的长期观察和认识。
正如梅老师所说,在北京清华大学的三年里,我从导师和朋友的监督和鼓励中受益匪浅。 例如,1935年夏天开学前,我第一次与蒋廷甫老师见面讨论选课问题时,蒋老师一开始就说,刘守民老师已经和他讨论过我一年级的科目了,所以他为我精心规划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的主要课程。 系主任对低年级学生的特别照顾让我感到很受宠若惊,这更加激发了我争先恐后的决心。
又如我的妹夫王尊明,多年后成为冶金专家(1935年七级毕业)。 赴美留学前,他曾在物理系担任助教。 由于家乡与江西省的关系,他几乎无所不谈。 吴老师曾开玩笑告诉他,我们班的状元李正武(1934年十级)在微积分课上经常不交作业,引起华罗庚老师的极大不满。 吴对华说:“不管他交不交功法,你放心,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的!” 这对资优学生是何等的关心和理解啊!
又如任志工先生在昆明接受采访。 虽然他从未给九年级尖子生林家桥(1937年毕业)教过普通物理,但系里的同事们经常回忆起,从1933年到1934年,林家桥是被选为数学家的一年级学生。 。 在洪东老师的普通物理季末考试中,萨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某个问题的所有可能答案,等着看林是否选择了最简单、最美的答案。 结果,林老师的回答出乎了所有教授的预料,比任何人预想的答案都要好! 这些只有亲身经历、亲耳听到的“轶事”,才能真正深刻地体现清华精神。

何丙迪与林家桥2010年在清华大学相识
当然,清华精神还体现在同学之间的相互支持。 我的性格有外向和内向之分。 一般来说,我不太愿意主动和学长同学“破冰”。 我在一二年级时的朋友圈较小,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开始与高年级的一些“知名人士”和三年级的研究生谈论职业和个人兴趣的。
首先要提的是当时经济系研究生徐宇男。 因为在系里教统计学的赵仁荣教授是我的亲戚,所以我经常去赵家吃饭。 看到书架上有很多数学专着,我就问他经济学家如何运用如此高深的数学。 赵老师很坦白地告诉我,他有一个好学生,徐宇男,但他的经济学知识只比徐展领先一两步。 如果他不努力学习,他很容易就会被徐战超越。 徐很快就通过了中英耿耿奖学金,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西文阅览室,我和徐总是斜坐在桌子对面,第三年我们终于进行了两三次认真的交谈。
又比如,政治系七级研究生陈明珠学长,积累了大量的留学考试经验。 他有洁癖,经常躲在门后。 当有人开门时,他总是先跳出去,以免碰到门上“肮脏”的把手。 他的绰号是“老恶魔”。 不知道为什么他最后主动告诉我他的考试经验和技巧,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政治学系八年级高年级学生金文翰向我讲述了基本功的重要性,并告诉我他已经读了八遍奥本海姆的《国际公法》,包括小注。 他最终获得了中文和英文的耿耿文凭,现在是复旦大学名誉教授。
又如闻一多先生的高年级学生孙作云,来自东北,日语非常好。 他的毕业论文《九歌山鬼考》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他给我讲了诗歌和神话。 7月7日后留在北平。 1938年底,他读了我在燕京《历史年报》中的《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由来》,给了我难忘的鼓励。
1937年春,被张慎甫先生特别称赞“文笔万字”、专攻德国哲学文学的李长治学长(长治)也多次与我谈论歌德的《少年的烦恼》。维特”和“浮士德精神”并鼓励我阅读和背诵更多的英语经典。 不久,他招收自己去追求北大美女许芳,并遭遇挫折。 我壮着胆子劝他冷静,指出许芳本身就是一个“才女”,不需要再有一个风流的学者、哲学家,多半会喜欢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武士。 没想到,原来徐芳逃亡台湾后,嫁给了中年儒将徐培根。
吴宓的书信和笔迹
李严本身是不朽的; 《言》的形式和内容都像一本日记,其史料价值特别高。 无宓大师的矛盾性格(浪漫主义诗人追求爱情却受到极其严格的道德标准),他深厚的中西古今文化修养,他长期倡导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他与陈寅恪大师一生的友谊和友谊。 那些钦佩的亲切记录,以及鼓励后进生的坦诚真挚的言行,都是我国20世纪的人文学者所熟知的,无需多言。 没想到,《吴宓日记,1936-1938》(北京:三联书店,1998)详细列出了我们的“初识”和交往。 吴老师的两年日记中涉及我的七条记录,不仅是我漫长的学术记忆中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体现20世纪30年代清华精神的最生动的例子之一。 相关文章转载如下:
[1936服]8月8日,星期六
晚上7点到9点,我独自坐在气象台看晚景,遇到了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丙迪(浙江)。 非常好的谈话。 米河君总结了他对中国近代历史和政治的总体看法;……米河君是这么认为的。 他的观点对年轻人来说是相当超然和有希望的。 米粒描述了尹柯的渊博学识,何君打算立即向尹柯请来。
8 月 17 日星期一
4-5 睡觉。 5:00 轩又来了。 潘光旦带着权增谷来了,但没有进屋。 7:00,何德奎(上海市工信部局局办公厅)和叔叔何丙弟如约抵达。 晚餐(西餐)在Mi's Place。 ……天色已晚,轩话太多,她疲惫不堪,神色焦急。 知米没有机会和何德奎说话,但米却对此感到厌恶。 9:00 何君等候出发。 ……
8 月 18 日星期二
前夕4-6何丙弟来了,要了很多好处,谈得还不错。
9 月 15 日,星期二
10-11am 何秉迪来了

3 月 15 日,星期一 [1937]
4:30-6:00何丙弟介绍何继来,米薇讲述《学衡》、《大公报文艺副刊》停刊的真相,以及碧流的轶事。 何济是何莲的弟弟,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7 月 4 日,星期日
早上8:00,何秉迪过来谈自己的学业计划。 一直到10点30分。
7 月 17 日,星期六
中午12-1点,拜访叶其孙。 路上遇见何丙弟,谈国难。
1936年秋季开学前,8月8日周末,立秋前夕,我第一次见到吴老师,聊了两个小时,暗自承认他是一个“有为青年”。 ” 60多年后,我读到它,感触之深,难以言喻。 也许是当吴老师问起的时候,我决定汇报一下我这两年的学习情况:按照蒋老师、刘老师、雷老师的教诲,我首先了解了方法、观点、分析、综合,以及最高的意境。借鉴西方历史的历史著作,为今后深入研究做准备。 参考国家历史。 由于所讨论的学术步骤的方向与吴教授强调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目的一致,所以一开始的谈话就有一种相互融洽的感觉。
恰逢8月中国科学会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何德奎渴望再次见到他的哈佛老朋友,所以我就约了,于是我们在8月17日晚上举行了一场晚宴。由于晚宴谈话被另一位女客人垄断了,我们第二天下午,在我拜访之后戴德奎为了表达遗憾,趁机向吴老师请教中西文史重要读物。 没想到,这场愉快的谈话又持续了两个小时。 最让我惊讶的是,1937年7月4日,即卢沟桥事变前三天,我早上8:00去见吴教授,谈我的“学习计划,直到10:30才走” 6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无法想象,我这个什么都不怕的“初生牛犊”,怎么会有这么多长达150分钟的“学习计划”。 更难以理解的是,我竟然和宇僧大师一样学识渊博。 一位通晓中西知识、阅历世间、识人的大师,能够自始至终耐心地听着,不至于心烦意乱。
唯一无法解释的解释就是:清华精神!
清华精神源于清华传统。 清华书院最初是为了培养学生去美国留学而设立的,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必定是一所文理并重的通识教育学校。 清华改制为国立大学后,特别是梅贻琦任校长后(1931年12月),清华得到了很大发展。 当时,国家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促进科学和工程学,但限制语法”。 MEI总统和教授协会仅对“促进科学与工程学”做出了强烈回应。 他们扩大了最初是科学学院的一部分的土木工程系,并共同建立了最初的大规模工程学院,并与新成立的机械和电气工程系。 但是他从不谈论“限制性语法”。 实际上,在1930年代,Tsinghua语法和法律房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除了在各个部门的一般加强外,教授的研究氛围比以前更加繁荣,“ Tsinghua University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不再适应研究结果,因此,新的学术季刊:“社会科学:” “必须创建。 冯·尤兰(Master Feng Youlan)和肖·冈夸大师(Master Xiao Gongquan)的两个全面的杰作《中国哲学的历史》和《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进一步反映出,就语法教学和研究而言,Tsinghua University在该国顶级大学中排名最高。
Tsinghua在1930年代的语法教学和研究的活力必须取决于其背后的学术理想,而Mei总统后来在他的1941年《大学解释》中发表了这一理想(发表在《 Tsinghua University杂志》上, 13,第1期,Tsinghua University III,主要要点在第10周年纪念日的第一卷中说明:
...一般知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 专业知识是为特殊职业做准备。 一般知识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滋养身体,而且是为了启发他人。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一般知识就是基础,专业知识就是目的。 社会需要的是通才,专家是第二。 当没有一般专业知识的专家来到人们身边时,结果将不是新朋友,而是对人民的负担。 这不是一般专业知识的合适术语。 这只有大学四年。 在这么短的四年中,有必要为通用知识和特殊知识做准备,并且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差异。 比中国资本少? 这就是为什么强调两者并不容易的原因。 由于必须消除强调专业的缺点,而同等重点的理论是阻碍且难以实施的,因此强调专业的原则仍然有效。
教学和接受通用知识不足是当今大学教育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今天,学习不能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个主要部门。 “常识”一词意味着学生为这三个主要部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单独拍摄,您将对每扇门有充分的了解。 综上所述,您将能够认识到这三个之间的联系,并突然意识到宇宙的广阔,许多类别,悠久的历史以及文化和教育的丰富性。 必须有一种一致的方法来理解复杂性,并且必须有一个因果关系和依赖性原则。 这称为概括。 如今,研究仅在学习的第一年才将研究分为学院和部门,并且可以进入专门的研究。 因此,那些从事一个人的人不知道两个和三个,或者只对两个和三个中的一个有半数的理解,这与一开始听说过的人一样。 近年来,西方的大学教育工作者还试图考虑到这一点,并提出补救措施。 基本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减慢分支机构和部门的年数,有些是从第三年开始的。 另一个是在第一学年添加“一般理论”课程。 我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足够,但是它们对于攻击错误也很有价值,可以用作未来改革研究的基础。 大学是一所大型机构,而其产生的人是专家,他们的工作很粗糙,还是他们知识渊博,全面,知识渊博并能够约会的通才? ……
在20世纪,我国的大学教育基于一般知识,仅持续使用专业知识。 从来没有像Mei大师那样坚持不懈和聪明的人。 在学校开始时,梅先生提出了一句著名的谚语:“所谓的伟人并不意味着建筑物,而是大师。” 只有大师才能掌握特殊设备,只有大师才能启发未来。 主人,这就是为什么Tsinghua大学的精神如此“伟大”的原因。
1930年代的一些Tsinghua教授的集合,从左到右:Chen Daisun,Shi Jiayang,Jin Yuelin,Sa Bendong,Xiao Qu,Ye Qisun,Ye Qisun,Sa Bentie和Zhou Peiyuan。
与MEI老师并肩合作,以维护通识教育和培养和培养大师级科学家的原则是Ye Qisun老师(1898-1977),他们负责科学教学和研究多年。 (我想在此注释中介绍杰作:“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石 - Ye Qisun和Science Masters of Science of Science of Science of Science of Science of Science of Yu Wu and Huang Yancom,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0年。以及非常广泛的报道:它描述了Ye先生对世界科学研究领域的长期不舒服探索,他为提高Tsinghua University的数学和科学教学和研究标准的努力,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年轻人根据Tsinghua University的说法,Tsinghua University的科学家和他在国外研究的诱因。 Ye先生是早期最大的科学技术网络的最重要的组织者。他自己的科学学院院长的薪水。 此事后来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演讲,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是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诺贝尔奖奖学金的Arthur H. Compton的骄傲而有能力的学生; Wu的博士学位论文于1923年完成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会议论文集)。 你们立即聘请了以广播研究而闻名的萨本邦(Sa Bendong)和理论物理学家周·佩尤恩(Zhou Peiyuan)。 此外,Zhao Zhongyao从东南大学毕业,并受到Ye Qisun的赞赏,并带到了Tsinghua University进行仔细的培训,他在1929年至1930年的美国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进行了“两个发现”。他们实际上是电子旋律对的产生以及电子旋律对之间的关系。 “歼灭现象” - 陈阳在数十年后认真评估了这两种现象的发现,并被认为是“绝对是诺贝尔奖级的工作”。 (Chenning Yang在2001年2月22日给我的一封信中的判决。有关全文,请参见Yang Zhenning的Yang Zhenning收集的作品,第2卷,东中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2页。杨对Zhao先生的英语评估在我在Tsinghua(1934-1937)的三年中,整个学校都认识到物理学部是最接近世界高级标准的部门,并且最能有能力发展未来的大师级才能,这是我在美国发表的研究贡献。 。 这并非没有道理。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外,如果有人问我谁,什么,何处和哪些词最能代表Tsinghua的精神(当然包括1937年至1945年的西南相关大学),我必须重申他已被认可。作为世界一流的应用数学大师,Tsinghua九于1965年秋季,高级同学林·贾Qiao(Lin Jiaqiao)从麻省理工学院(MIT)来到芝加哥大学,进行了一周的学术讲座和对话。 当他在九年级物理学毕业生郭小兰的家中与我握手时,他说的话很快获得了美国气象学学会的最高奖项:“我们已经有几年了几年了。事情是,无论您从事哪种工作,您都不得提出二等问题。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本站,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lfxindamf.com/html/tiyuwenda/2902.html